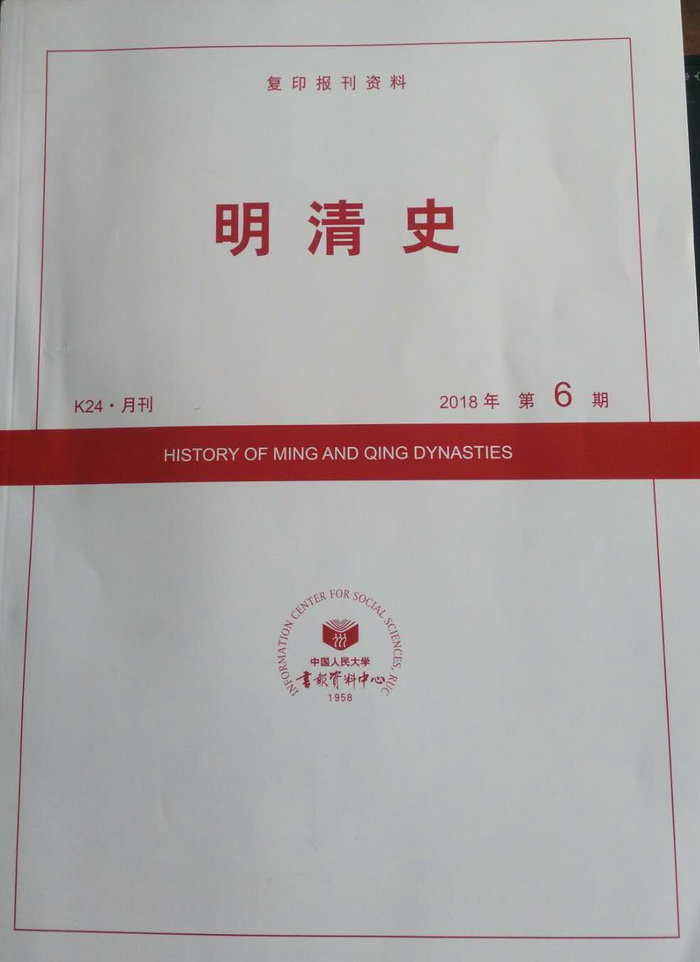注释:
①[日]大塚义雄:《共同体的基础理论》,于嘉云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年,第4页。
②钞晓鸿:《灌溉、环境与水利共同体——基于清代关中中部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钱杭:《共同体理论视野下的湘湖水利集团——兼论“库域型”水利社会》,《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③[日]丰岛静英:《中国西北部にずけ水利共同体にいて》,《历史学研究》第201号,1956年,第23~35页。
④有关这方面较重要的论著有:哈斯巴根:《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区域研究(1697-1945)》,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闫天灵:《清代及民国时期塞外蒙汉关系论》,《民族研究》2004年第5期;王晗:《清代毛乌素沙地南缘伙盘地土地权属问题研究》,《清史研究》2013年第3期等。
⑤严格意义上来说,自清康熙三十六年放垦以后,“禁留地”这一概念便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其衍生概念如“牌界地”“黑界地”等。为了研究方便,本文仍以“禁留地”概念来指代该地域。
⑥[民国]张鹏一:《河套图志》卷5《水陆交通》,内蒙古图书馆藏抄本。
⑦张力仁:《民国陕绥划界风波述论》,《人文杂志》2016年第10期。
⑧《清圣祖实录》卷181,“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乙亥”,中华书局,1985年。
⑨“伙种”“伴种”或“合种”,是传统小农经济中两人以上农民为补充各自劳动之不足而形成的一种协力、合作经营单位。参见[日]今堀诚二:《农村合伙诸形态》,《中国封建社会构成》,日本学术振兴会刊,1978年;[日]铁山博:《清代农业协理共同关系——“伙”诸形态》,《清代农业经济史研究》,御茶水书房,1999年。
⑩[清]王致云修,朱壎纂:《神木县志》卷3《建置上·附牌界》,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11)《神木理事司员衙门为审办越界垦种之事札准格尔旗贝子文》(道光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金海等编译:《准格尔旗扎萨克衙门档案译编》(第一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以下乾隆、嘉庆、道光时期档案资料出处同此,不复注)。
(12)[法]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耿升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第221页。
(13)张植华:《清代蒙汉关系小议》,《内蒙古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14)[日]安斋库治:《蒙疆土地分割制的一个类型——伊克昭盟准格尔旗河套地土地关系的特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1942年,第10~11页。
(15)《神木理事司员衙门为遵照理藩院饬令严惩擅自招募民人越界耕种事札准格尔旗贝子察克都尔色楞及协理台吉等文》(道光十九年二月初四日);《盟长棍藏拉布坦扎木苏为审理蒙古伙同民人耕种事札扎萨克贝子察克都尔色楞及协理台吉等文》(道光二十五年七月二十日)。
(16)《偏关县令为查处所属民人与蒙古勾结私行耕种事咨准格尔旗贝子文》(道光五年三月十一日)
(17)郭松义:《清代农村“伙种”关系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
(18)[清]李熙龄纂修:《榆林府志》卷3《舆地志·疆界附边界》,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19)蒙藏委员会调查室编印:《伊盟右翼四旗调查报告书》,1939年,第49~50页。
(20)《乾清门行走盟长扎萨克多罗贝勒纪录二次的索德纳木喇卜寨根顿致扎萨克贝子纪录一次的茶客多尔色楞及协理台吉等书》,511-1-11。
(21)蒙藏委员会调查室编印:《伊盟左翼三旗调查报告书》,1941年,第25页。
(22)《扎萨克察克都尔色楞为禁止蒙汉民私行开垦地亩呈神木理事司员衙门文》(道光十四年三月末)。
(23)《神木理事司员衙门为结案札准格尔旗贝子文》(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初四日)。
(24)[法]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189~190页。
(25)除非特殊情况下如以租抵债,需要特别约定有关事项的,蒙汉双方才订立文书契约。如乾隆五十四年,喇嘛昭都巴与民人梁广富约定四年后债清地归原主(见道光五年三月二十九日《神木理事司员衙门为审理府谷县旧案札准格尔旗协理台吉等文》)。
(26)《扎萨克贝子查克都尔色楞及协理台吉等为民人抗阻一事呈神木理事司员衙门文》(道光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27)《扎萨克贝子察克都尔色楞及协理台吉等为地租银两事咨河曲县衙门文》(道光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28)《扎萨克贝子察克都尔色楞为征租地银两事咨府谷县知县衙门文》(道光二十六年夏)。
(29)“黑界地”为清乾隆年间为限制、区分、查禁民人耕地与蒙旗耕牧而划定的“朝廷禁垦之地”,其性质类似清初设定的“禁留地”。
(30)咸丰八年六月二十日《扎萨克贝子扎那济尔迪、协理台吉等为黑牌子界地内民人拒不交纳租银事呈神木理事司员都统衙门文》,金海等编译:《准格尔旗扎萨克衙门档案译编》(第二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以下咸丰、同治时期档案出处同此,不复注);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伊克昭盟长为民人拒交官租事咨托克托厅通判衙门文》,金海等编译:《准格尔旗扎萨克衙门档案译编》(第三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以下光绪、宣统时期档案出处同此,不复注)。
(31)《神木理事司员为审理民人非法占据土地并霸占蒙古妻儿等事件札准格尔旗文》(道光八年二月初一日)。
(32)《尚书班第、总督根福奏为复议榆林附近民人口外耕地并定界加租恭折》(乾隆八年十二月初七日)。
(33)道光《榆林府志》卷3《疆界附边界》)。
(34)[清]郑居中纂修:《府谷县志》卷2《田赋·附人民租种五堡口外蒙古鄂尔多斯地土内》,乾隆四十八年刻本。
(35)[清]何炳勋纂修:《增修怀远县志》卷4《边外》,道光二十二年刻本。
(36)[清]丁锡奎纂修:《靖边县志稿·凡例》,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37)《乾隆朝实录》,“乾隆元年三月丁己”条,中华书局,1985年。
(38)《前绥远垦务总局资料——伊克昭盟·准格尔旗》整理番号38,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地政总署,1940年。
(39)这一行政管理体系的实质是,蒙人归属盟(蒙)旗管理,民人归内地州县“境外管理”或“遥治”,而对蒙汉交涉事务则由既无属土亦无属民的宁夏、神木的理事司员衙门管理。梁卫东:《清代汉族移民与鄂尔多斯行政体制重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40)《陕北榆绥延鄜公民代表呈文》(民国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樊士杰等编:《陕绥划界纪要》卷1,1932年,铅印本。
(41)廖兆骏:《绥远志略》,正中书局,1937年,第16页。
(42)《尚书班第、总督庆复奏为有关鄂尔多斯开垦事宜之折》(乾隆八年十二月初七日),准格尔旗扎萨克衙门档案,001-1,A001-3,22。
(43)宝玉:《清末绥远垦务》,内蒙古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室印:《内蒙古史志资料选编第一辑》(下)(内部资料),1985年,第19页。
(44)贻谷:《绥远奏议》,《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103册,台湾文海出版社,1984年,第326页。
(45)(46)(48)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8、538、537页。
(47)贺扬灵:《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08~110页。
(49)哈斯巴根:《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区域研究(1697-1945)》,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9~221页。
(50)按各旗所放土地岁租的分配比例不一。如扎萨克旗,“所征岁租二成归公,二成存储,其余六成拨归该旗”;民众抗垦较严重的乌审旗“所收岁租先提经费一成,其余分作十成,二成存储,八成拨归该旗”。参见民国《河套新编》之《河套垦务调查记》)。
(51)(53)贻谷:《绥远奏议》,《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1辑,第103册,文海出版社。
(52)绥远通志馆:《绥远通志稿》卷42《农业》,1935年初稿,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
(54)《前绥远垦务总局资料——伊克昭盟·准格尔旗》整理番号23,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地政总署,1940年。
(55)张乐轩:《伊克昭盟志》第11章《郡王旗》第7节《农民与商人》,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之六,远方出版社,2007年。
(56)张乐轩:《伊克昭盟志》第10章《扎萨克旗》第7节《农垦》。
(57)《郡王旗协理台吉布仁吉尔格勒致准格尔旗协理等书》(光绪二十八年),511-1-84。
(58)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0页。
(59)苏德:《清末伊克昭盟郡王旗西界地亩禁闭一案始末》,内蒙古档案局、内蒙古档案馆编:《内蒙古垦务研究》(第一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
(60)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5页。
(61)贻谷《蒙垦陈诉供状》附鹿传麟、绍英《奏为查明垦务大臣被参各款谨分别轻重据实胪陈并保荐贤员办理善后事宜以绥蒙藩而收实效折》,《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一辑,第820页。
(62)《前绥远垦务总局资料——伊克昭盟·准格尔旗》整理番号62,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地政总署,1940年。
(63)《前绥远垦务总局资料——伊克昭盟·准格尔旗》整理番号88,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地政总署,1940年。
(64)《准格尔旗为驱逐农民社首领楼四等事咨神木同知衙门文》(宣统元年七月二十日)。
(65)《准格尔旗为该旗民人成立农民社事呈盟长处文》(宣统元年十月二十二日)。
(66)[民国]宋伯鲁等修,无廷锡等纂:《续修陕西通志稿》卷28《田赋三》,1934年刻本。
(67)哈斯巴根:《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区域研究(1697-1945)》,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9页。
(68)《盟长栋罗布色稜为从速办案札饬扎萨克贝子色旺喇什文》(乾隆五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69)《神木理事司员为查禁旗地札准格尔贝子文及其复文》(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70)吴承忠、韩光辉、舒时光:《清陕西内蒙“黑界地”的由来与发展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71)《托克托厅通判衙门为办理越界耕种蒙地民人事咨准格尔旗贝子文》(嘉庆七年六月初二日)。
(72)《准格尔旗协理台吉等为据实呈报嘉庆十八、十九年土地开垦情况呈神木理事司员及盟长处文》(道光四年闰七月二十六日)。
(73)《遵命驻神木处理蒙汉交涉案件同知觉罗吉致鄂尔多斯准格尔扎萨克贝子等书》(道光九年三月十日),A008-1,001,39。
(74)《盟长处为转行理藩院责令延榆绥道员、神木理事司员、伊克昭盟盟长三方会审准格尔旗私行招民垦种案札饬准格尔旗文》(道光六年十月初三日)。
(75)《前绥远垦务总局资料——伊克昭盟·准格尔旗》整理番号62,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地政总署,1940年。
(76)《准格尔旗贝子为其外出之际旗地被民人耕种殆尽之事呈盟长处文》(道光十年闰四月十五日)。
(77)《盟长处为转行神木理事司员衙门之禁令札准格尔旗协理台吉等文》(道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78)《盟长处为转行理藩院宣谕惩处私行招民垦种之新定律例札准格尔旗协理台吉等文》(道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79)据记载,道光五年、六年、八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准格尔旗放垦“黑界地”蒙人数分别为182人、65人、75人、201人、242人、250人。见《道光五年至十二年间放地招民之蒙人名单》(道光十三年)。
(80)《神木理事司员为严禁私招民人开垦旗地札准格尔旗贝子文》(道光十三年三月十六日),《盟长棍藏拉布坦扎木苏为出关巡查旗地时查出私行招募民人耕种封禁土地事札准格尔旗贝子察克多尔色楞、协理台吉文》(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81)绥远城将军升寅《奏报伊克昭盟鄂尔多斯有关办理土地阿勒巴面二事来京控件要陈》,道光十年八月二十二日(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4/322/1。转引自祁美琴:《伊克昭盟的蒙地开垦》,《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4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
(82)《前清门行走副盟长鄂尔多斯扎萨克贝子色旺喇什致驻神木处理蒙汉交涉案件理事司员书》(嘉庆六年三月八日),001-1,A003-3,54-24。
(83)《神木理事司员衙门为将私行耕种所得收成没收入官之事札准格尔旗协理台吉文》(道光六年八月十六日)。
(84)《神木理事司员为严禁私招民人开垦旗地札准格尔旗贝子文》(道光十三年三月十六日)。
(85)《神木理事司员衙门为抓捕越界垦种民人事札准格尔旗贝子察克都尔色楞文》(道光二十年三月十一日)。
(86)《副盟长扎那济尔迪为开垦黑牌子界地以救济旗民事咨神木同知衙门文》(光绪四年六月初六日),《准格尔旗为知会已放垦该旗南部荒地事咨同知衙门文》(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
(87)《准格尔旗为无法遵照指令拘留私行耕种之涉案人候审一事呈盟长处文》(道光五年十二月初九日)。
(88)《神木理事司员衙门为会审蒙古伙同民人耕种一案札准格尔贝子察克都尔色楞文》(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初九日)。
(89)《绥远通志稿》卷38《垦务》。
(90)《道光十四年往来文书挡册》(道光十四年三月十日)。转引自哈斯巴根:《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区域研究(1697-1945)》,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9页。
(91)《副盟长察克都尔色楞及协理台吉等为押送涉案人员事呈绥远将军衙门文》(道光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92)《神木理事司员衙门为饬令核查新旧界牌地一事札准格尔旗协理台吉等文》(道光五年八月初一日)。
(93)《神木理事司员衙门为催促报送黑牌子界地原定旧档之事札饬鄂尔多斯扎萨克固山贝子察克都尔色楞及协理台吉等文》(道光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
(94)《盟长处为谨慎对待耕种面积及非法招引民人耕种事札准格尔旗协理台吉等文》(道光六年二月二十日)。
(95)《副盟长扎萨克贝子喇什多尔济、协理台吉等致鄂尔多斯准格尔旗扎萨克贝子书》(乾隆五十九年四月二十日),001-1,A002-8,20-4。
(96)《伊克昭盟长为民人拒交官租事咨托克托厅通判衙门文》(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
(97)《准格尔旗为办理民人拒不交纳地租案咨神木同知衙门文》(光绪十五年十月十八日)。
(98)《准格尔旗地租记录》(光绪十四年)。
(99)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1958年,第3956页。
(100)“独贵龙”,是清代伊克昭盟蒙古族民众反帝反封建的一种独特形式。参加“独贵龙”的群众到约定的地点会议,与会者坐成圆圈共同讨论斗争的问题,并在讨论通过的决议上,或在给王公官府的呈文上签名成圆圈,以示不易暴露领导者。“独贵”在蒙语中是圆的意思,“独贵龙”一词也是由此意而来。
(101)贻谷:《蒙垦续供》,《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
(102)贻谷《蒙垦陈诉供状》附鹿传麟、绍英《奏为查明垦务大臣被参各款谨分别轻重据实胪陈并保荐贤员办理善后事宜以绥蒙藩而收实效折》,《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一辑,第820页。
(103)“咨议王承朴条陈”,《农商公报》106期,《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二辑,第663~6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