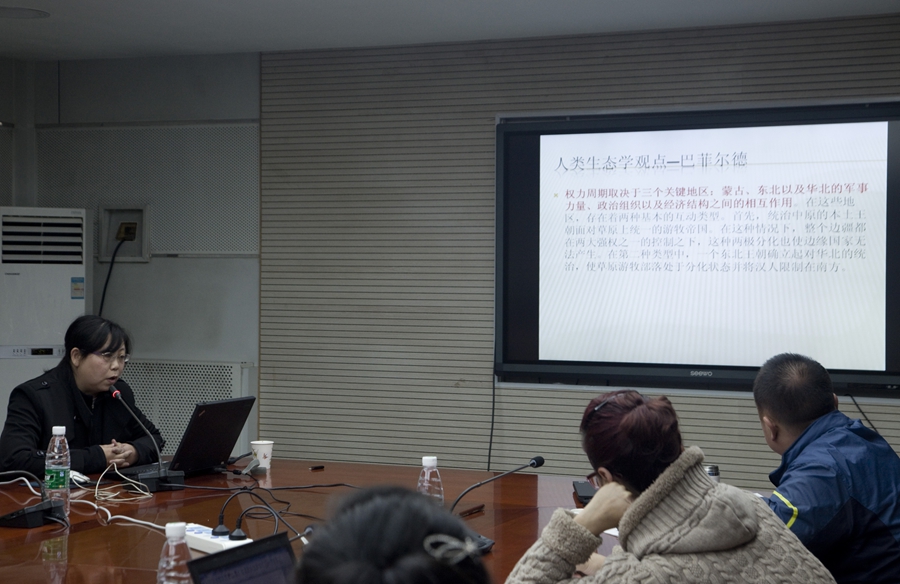在本院张莉博士和崔建新博士的召集下,2015年11月06日14:30—18:00,于雁塔校区崇鋈楼敏行厅举办了“边疆变动:气候、制度与族群”学术沙龙活动。来自我校历史文化学院的艾冲教授、孟洋洋博士生,我校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的黄达远、徐百永、王启明等老师及部分研究生,西北大学的张健博士,以及我院的高升荣、聂顺新、张青瑶、杜娟、屈雅婷等青年教师和部分研究生共济一堂,以“边疆研究”为核心,围绕“新清史”、“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史观”、“气候变化、族群迁徙、制度变更对边疆的影响”等问题展开充分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
沙龙首先由张莉博士从自己近两年的读书和思考谈起,提出应该从西方历史学史的角度出发理解作为“新史学”之一的“环境史”内涵及其学术意义。继而提出,我们应该反思“新清史”、“民族主义史学”话语下构建的边疆史,思考如何将研究视角从“由中心到边缘”转变为“由边缘对边缘”、“由边缘到中心”,深刻揭示边疆的区域性社会-文化结构特性,把握气候、制度、族群互动下边疆变动的共性和特性、断裂和连续等问题。
随后,艾冲教授做了题为“鄂尔多斯高原东汉时期的民族迁徙与分布”的主题发言。艾冲教授主要从“南匈奴八部的分布暨单于庭的迁入”、“乌桓族诸部的西移及迁入‘河南地’”、“鲜卑诸部的南迁及进入‘河南地’”、“羌族部落的东迁及分布区的扩展”、“‘河南地’汉族人口的迁徙、分布与数量”等五个方面向我们介绍了东汉时期多个民族迁入和迁出鄂尔多斯高原地区的复杂历史过程,最后呈现出不同于西汉时期的民族构成与空间分布新特征。
紧接着,黄达远教授进行了题为“从边缘到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新史观”的发言,黄达远教授重点谈到了两种新疆历史的书写——国家地方史和地方民族史——中存在的矛盾,指出我们应该提出一种“新史观”,目前可以用区域史观来重新审视边疆的历史,将被压缩、淡化和均质化了的边疆内部文化区域的差异性、多样性、多元性、共生性揭示出来,呈现出边疆历史的流动性、复杂性,建立一种复线历史叙述。
徐百永博士以“边疆话语下的近代西藏书写”为题,向我们了介绍了西藏如何进入民国学人的知识视野、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边疆”概念的出现及对西藏的边疆认知、民国学人对清代西藏知识的继承、对英国西藏知识的翻译等都与他们的西藏历史书写息息相关。最后,徐百永博士指出,民国中央政府与西藏的疏远关系、内地与西藏的交通阻隔等是影响民国西藏书写内容的另一个重要层面。
崔建新博士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向我们介绍了“人类生态学视野下的中国边疆研究”。结合自己读书和科研状况,崔建新博士分别阐述了拉铁摩尔、巴菲尔德、濮德培以及王明珂关于“中国边疆”的不同理解和他们各自独特的边疆区域划分。她指出这些学者的思想事实上是具有一脉相承性的,但各自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拉铁摩尔强调草原地带是游牧经济和政权的动力策源地,巴菲尔德的边疆区划中着重分析东北地区生态多样性与满洲崛起的关系,濮德培则指出内亚边疆内部纬向交流的重要特性和区域生态系统多样性对游牧政权崛起的作用,王明珂强调人类生态也是一种历史本相、从边缘看中心的独特视角、游牧业是一种精细化程度很高的生产方式等等。崔建新博士认为,所有以上人类生态学观念中都强调生态缓冲区的作用,但是对于中国边疆地区之间的地理差异与边疆变动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更加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随后,她简要介绍了她对鄂尔多斯高原上的统万城兴废与气候变化、沙漠化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对明清之际东北气候变化、农业收成与满洲崛起的初步分析,指出气候因素的降水变化对草原族群的影响较大。
最后,孟洋洋博士生做了题为“东汉度辽将军府驻地考实”的主题发言。孟洋洋从三个方面对度辽将军府的驻地进行了论证,得出其位于黑庆壕古城的观点。此外,作为对《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地的回应,孟洋洋从三个方面反驳了城圪梁古城是度辽将军府驻地的说法。
在短暂的茶歇过后,沙龙进入圆桌讨论阶段。张莉博士倡导大家围绕“史料的拓展”、“学术视野的拓展与国际学术对话能力的提升”、“学术理论与方法”、“如何提出新的学术问题”等方面展开讨论未来如何深化边疆研究的问题。王启明博士从“制度”和“新史料”的角度对沙龙话题进行了回应,指出在晚清时局冲击下,新疆由军府制向行省制的转变,因而应该改变目前对行省制度的静态的、表象的历史描述,走向系统化的深入研究,重视对新出地方档案史料中边疆基层社会组织体系等问题的研究。黄达远教授指出历史地理学是塑造民族主义的重要工具之一,现代化历史的核心是民族国家的历史,目前我们的研究面临着挑战,边疆的历史研究也进入到一个尴尬的境界,我们应该反思西方社会理论中民族主义将土地和固定的人群结合、固化而出现的民族主义历史书写、反思我们接受苏联知识体系(以语言学为中心)而出现的民族史书写,建立更加自主性的话语体系,才能够呈现出中国历史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独特性。艾冲教授分别对之前各位老师的发言进行了评议,指出对西方学者的观点要慎审对待,要有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进行边疆研究,同时建议研究生做具体的研究,注重史料范围的开拓。随后,大家围绕着“中国的内涵”、“历史上的边疆范围”、“气候变化对族群变动的影响”、“中西方历史研究出发点和路径的差别”、“其他语言历史资料的使用”、“王朝国家向近代国家转型之际中外力量的多重影响”、 “为什么鄂尔多斯高原会成为边疆冲突的前沿”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流和对话。
此次讨论,与会师生深切感觉到历史地理与社会科学结合成为一个重要的知识方向,一方面要和西方社会理论对话,另一方面加强与民族学、人类学之间跨学科的互动,可以大大提升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维度。最后,参与本次沙龙活动的各位师生都表示期待类似的学术活动再次举办,以促进多学科研究方法与视角的交叉与交流,推动边疆研究的深化。